目录
快速导航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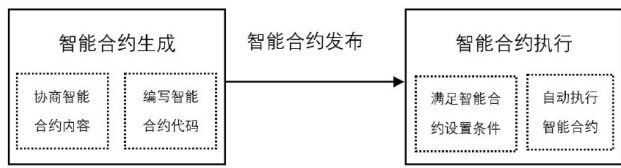
理论探讨 | 区块链平台轴辐类算法共谋风险及其反垄断规制
理论探讨 | 区块链平台轴辐类算法共谋风险及其反垄断规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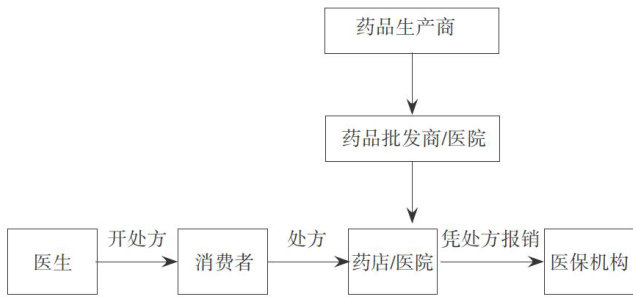
理论探讨 | 专利药品相关市场界定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
理论探讨 | 专利药品相关市场界定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
-
理论探讨 | 基于不当得利制度的商标强制移转请求权构造
理论探讨 | 基于不当得利制度的商标强制移转请求权构造
-
理论探讨 | 禁止重复注册商标的理论重构与规则再造
理论探讨 | 禁止重复注册商标的理论重构与规则再造
-
数字法治 | 从宁波森浦案看数据垄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制定路径
数字法治 | 从宁波森浦案看数据垄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制定路径
-
数字法治 | 算法解释权的法理反思与赋权限制
数字法治 | 算法解释权的法理反思与赋权限制
-
人工智能治理 | 生物特征识别型人工智能的规制:欧盟模式与中国方案
人工智能治理 | 生物特征识别型人工智能的规制:欧盟模式与中国方案
-
青年论坛 | 平台规则的二元属性及其合法性控制
青年论坛 | 平台规则的二元属性及其合法性控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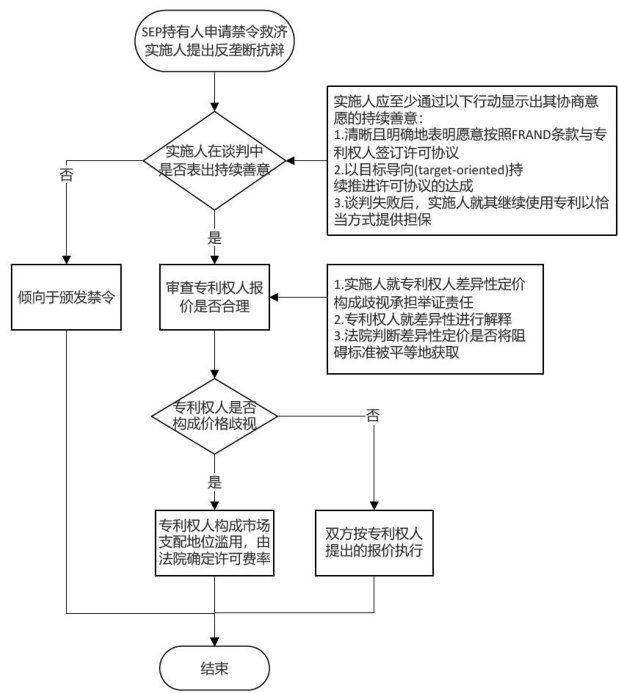
青年论坛 | 反垫断法视角下SEP善意许可谈判的标准
青年论坛 | 反垫断法视角下SEP善意许可谈判的标准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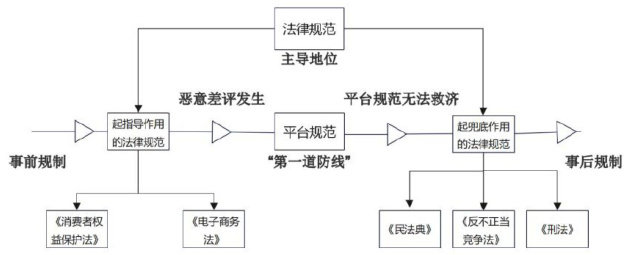
青年论坛 | 法律激励理论下的网购恶意差评法律规制
青年论坛 | 法律激励理论下的网购恶意差评法律规制
-
青年论坛 | 反不正当竞争领域“技术中立”的逻辑定位
青年论坛 | 反不正当竞争领域“技术中立”的逻辑定位
-

英文版 | Fritz Machlup's Verdict 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Patent System 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Reality
英文版 | Fritz Machlup's Verdict 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Patent System 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Reality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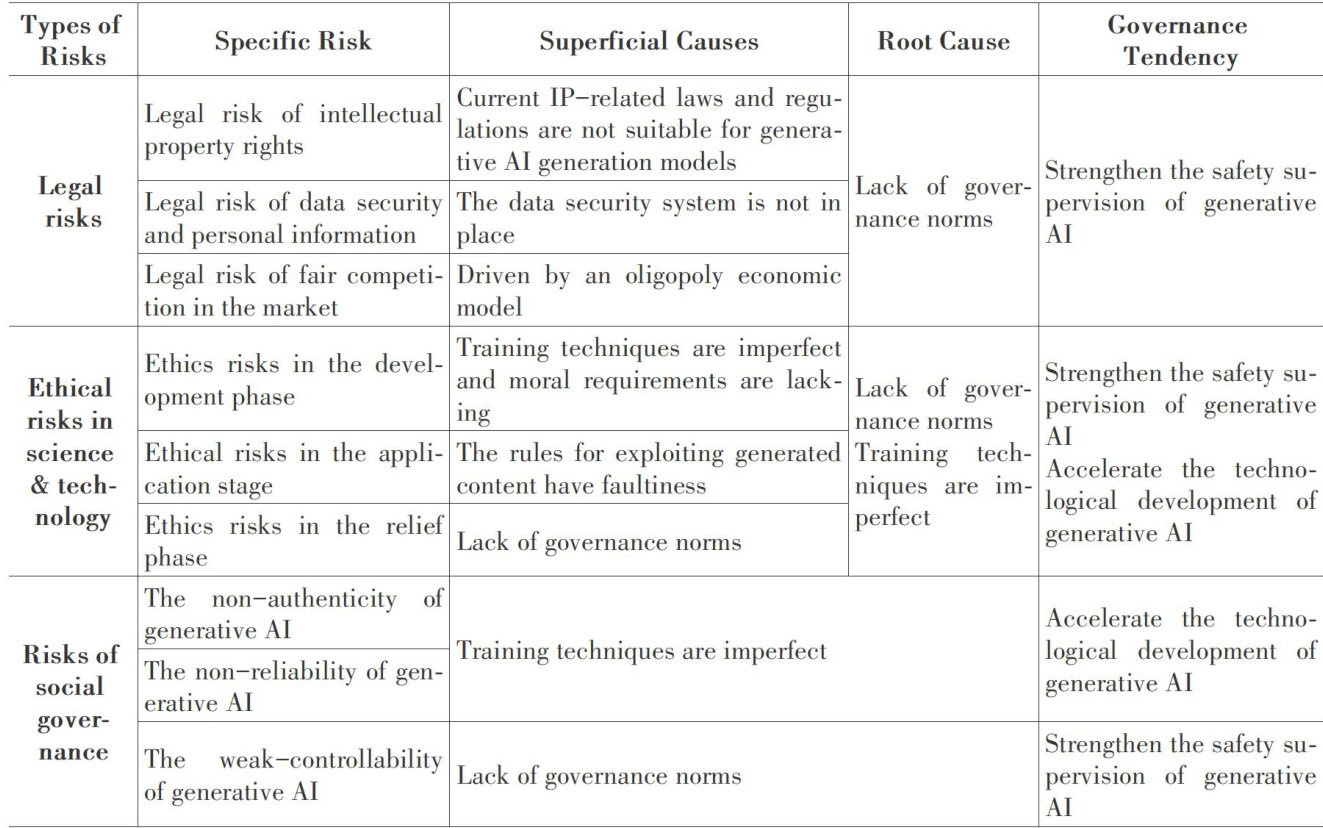
英文版 | Legal Framework and Its Practice for the Normativ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I in China
英文版 | Legal Framework and Its Practice for the Normativ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I in China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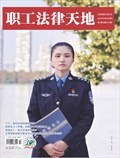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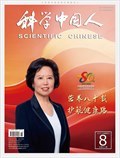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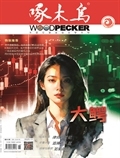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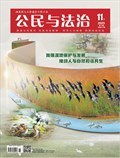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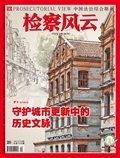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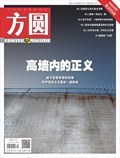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