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
特别推荐 | 电诈园(长篇小说连载)
特别推荐 | 电诈园(长篇小说连载)
-
特别推荐 | 创作谈:县城万象
特别推荐 | 创作谈:县城万象
-

纪实作品 | 祖旭的故事
纪实作品 | 祖旭的故事
-

好看小说 | 在东山
好看小说 | 在东山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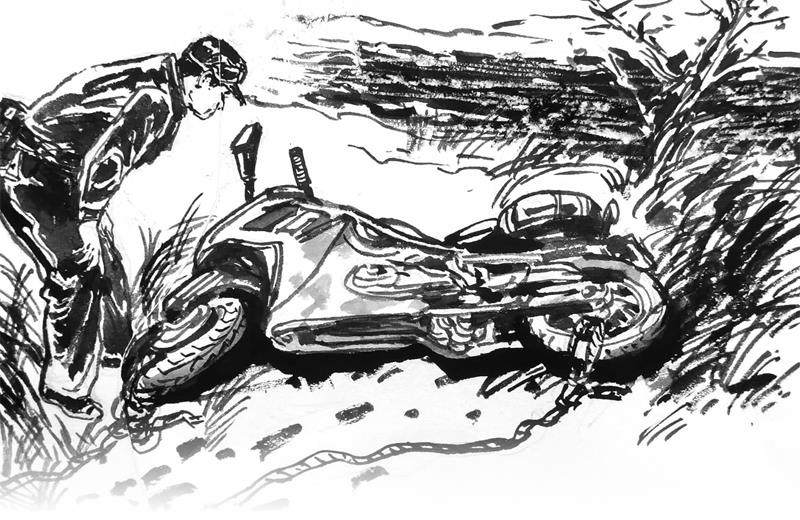
好看小说 | 墙里家外
好看小说 | 墙里家外
-

侦探与推理 | 请让文物先说
侦探与推理 | 请让文物先说
-

我与《啄木鸟》的故事 | 我与21世纪之初的公安文学
我与《啄木鸟》的故事 | 我与21世纪之初的公安文学
-
散文随笔 | 活成舅舅的样子
散文随笔 | 活成舅舅的样子
-

散文随笔 | 身在唐家河
散文随笔 | 身在唐家河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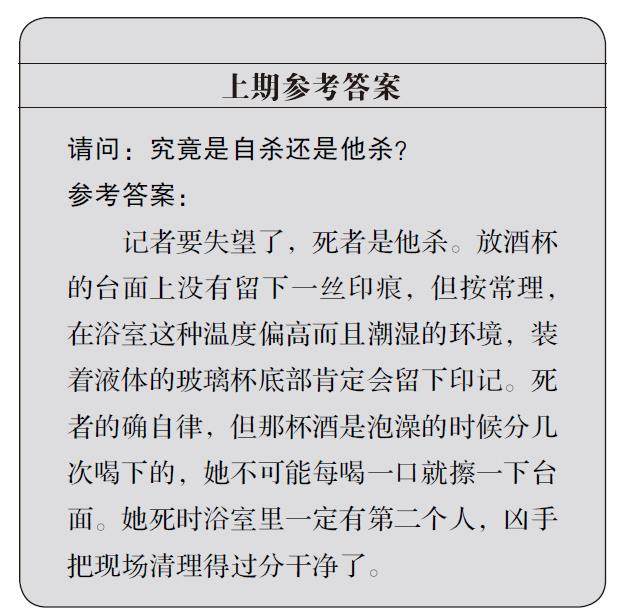
侦探俱乐部 | 试镜
侦探俱乐部 | 试镜



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