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
新名家 | 一棵树,或者一个信封(组诗)
新名家 | 一棵树,或者一个信封(组诗)
-

原浆散文 | 晚饭花旁的晚饭
原浆散文 | 晚饭花旁的晚饭
-

原浆散文 | 模模糊糊的路
原浆散文 | 模模糊糊的路
-

原浆散文 | 让火燃烧它们的精神
原浆散文 | 让火燃烧它们的精神
-

原浆散文 | 磨铣记
原浆散文 | 磨铣记
-

原浆散文 | 目字旁
原浆散文 | 目字旁
-

原浆散文 | 如何制作一个爸爸
原浆散文 | 如何制作一个爸爸
-

原浆散文 | 女儿红
原浆散文 | 女儿红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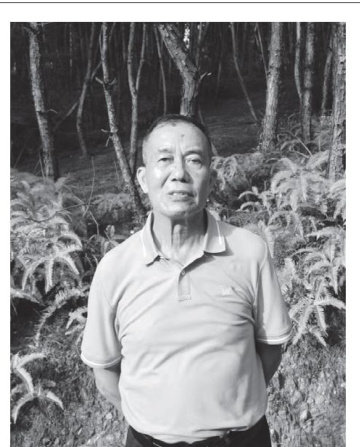
原浆散文 | 回家
原浆散文 | 回家
-

原浆散文 | 『男一号』
原浆散文 | 『男一号』
-

原浆散文 | 土豆一样的女人
原浆散文 | 土豆一样的女人
-
魅力小说 | 钻井队逸事
魅力小说 | 钻井队逸事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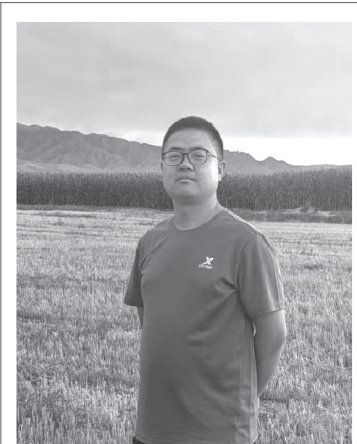
魅力小说 | 韦伯的垃圾时间
魅力小说 | 韦伯的垃圾时间
-

魅力小说 | 不会死去的父亲
魅力小说 | 不会死去的父亲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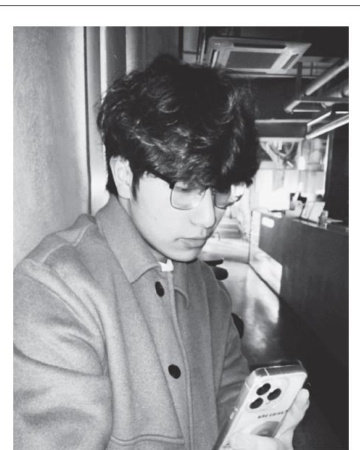
第一声 | 欢乐
第一声 | 欢乐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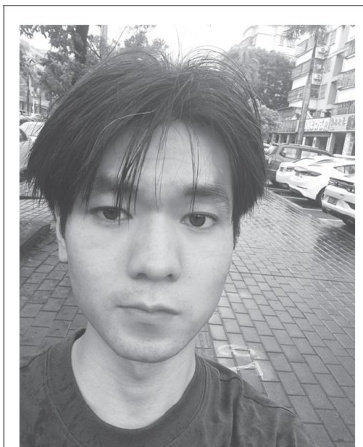
第一声 | 一个秋日的午后
第一声 | 一个秋日的午后
-
蝉的地下时光 | 我的文学小径
蝉的地下时光 | 我的文学小径
-
蝉的地下时光 | 在路上
蝉的地下时光 | 在路上
-
香樟诗会 | 香樟诗会
香樟诗会 | 香樟诗会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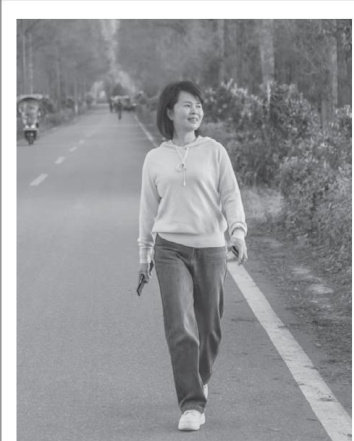
驿站故事 | 潦河边的课堂
驿站故事 | 潦河边的课堂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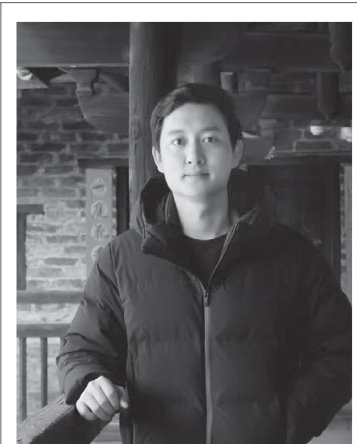
驿站故事 | 梅岭下最燃的七月
驿站故事 | 梅岭下最燃的七月
-
读者说 | 读者说
读者说 | 读者说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